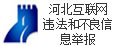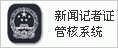近期,在邢邑镇邢邑村,一部80余万字的《邢邑村志》正式发行,成为定州市首部正式出版的村级志书。这部耗时7年完成的巨制,不仅填补了地方文化史的空白,更凝聚了以八旬老人李新国为代表的编修团队的心血与坚守。
2016年5月,邢邑村启动村志编修工作,退休干部李新国毅然扛起参与编修《邢邑村志》的重任。彼时的他未曾想到,这份“发挥余热”的差事,将会成为他晚年生活的全部重心。
邢邑村历史悠久,诞生过廉颇、刘琨、刘禹锡等历史名人,但大量古迹在岁月中损毁,资料散佚严重。“没有村志,后人永远不知道脚下土地藏着多少故事,如果我们这一辈人不在了,村庄的历史与记忆也会随着一起消失。”谈及初衷,李新国语气平淡,眼神中却透着坚定。
编修伊始,困难重重。编修团队最初由2名退休教师、2名退休干部、1名省级非遗传承人组成。团队组建后,1名退休干部因病退出,后又增补了2名。“虽然工作了大半辈子,但我们都没写过书,更没写过志书。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,比如体例怎么设计,章节怎么规划,文字怎么表述……当时这些问题让我们一筹莫展。”李新国回忆道。
在众人犯难之际,定州市原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韩振京搭好了整部志书的框架,拟定出整部志书篇目。有了方向,李新国就带领团队白天走访调研,夜晚伏案整理。“涉及人名必须直呼其名,不能用‘同志’,‘大概’‘可能’这类词统统删掉。”李新国对志书真实性近乎苛刻。
为核实“1942年邢邑肉丘坟惨案”的细节,李新国独自骑车到墓地抄录碑文,最终将坊间流传的活埋18人修正为17人。“真实是志书的生命,来不得半点虚假,错一个字就是对历史的不负责。”他说。
在推动村志编修工作时,李新国采取“群众口述、编辑记录、全民参与”的模式,邢邑村上至耄耋老者、下至青年学生,近至乡邻、远及海外,都积极撰写回忆文字、提供历史资料。
“村民口述的内容也不能直接放到村志之中,还要经过整合,把细碎零散的口头语变得系统连贯。”李新国说。
一沓沓泛黄的族谱、一张张模糊的老照片、一段段口耳相传的典故……李新国将零散的历史碎片逐一拼接。期间,六易篇目,五改志稿,硬是将零散的口述与残卷梳理成81.5万字的系统记录。
编修村志不仅是文化工程,更是对责任与初心的考验。2020年,当首版样书出现整页空白时,印刷厂试图以“增补材料”搪塞。李新国拍桌力争:“村方投资了30多万元,必须重排!”最终迫使印刷公司重新排版。
编修过程中,质疑声从未间断。“上级和村里给了你多少钱?”面对村民追问,李新国总笑着摆手“一分没有。”事实上,村委会7年累计补贴编修团队仅3500元,而团队成员的交通、通讯费用全是自费,李新国每月手机话费超百元,却从未向村里提过报销。
2022年9月,首本《邢邑村志》正式交付,当志书捧在手中时,这位82岁的老人湿红了眼眶。
翻开厚重的志书,那些熟悉的地名、人物、故事仿佛穿越时空而来,字里行间流淌的不仅是邢邑2600年的历史脉络,更是一位退休老干部对故土的深情与担当。
《邢邑村志》不仅是乡土历史记忆的复原,更实现了从“寻根”到“续脉”的跨越。书中记载的“晋察冀八中遗址”已获批市级保护单位,“邢邑平氏剪纸”也被批准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,沉睡的红色记忆与民间艺术重焕生机。更令人振奋的是,抗战时期“冀中军区回民支队”在邢邑整军命名的史实被首次披露,历史记忆的重现,为村庄增添红色荣光。
七载寒暑,鬓发尽霜。李新国用2500多个日夜诠释了“文化守望者”的担当。当年轻一代翻开书页,触摸到的不仅是文字,更是一群老人留给子孙的文化薪火照亮乡村振兴的长路。
记者刘子祎